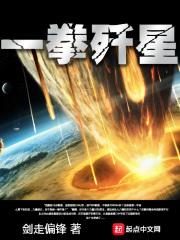言情小说>先生与朝暮讲的什么 > 第161頁(第1页)
第161頁(第1页)
於是沒過多久,他身上就胖了不少,起碼有五斤!
溫槿無奈。
許父許母和溫母陳寅早在溫槿出院後的第二天就回了南城,溫槿當時本想跟著一起去。但是長途勞累,他本來就不怎麼喜歡坐飛機,這事便暫時擱置了下來。
所以在溫槿的身體逐漸轉好之後,溫槿又和許溪舟提了一遍。
許溪舟問他:「是想回南城,還是回宜縣?」
他果然還是最懂他的。
「宜縣。」溫槿說。
來重海之後溫槿就沒回過南城了,宜縣還只在去年過年的時候回家去住過一天。
他的工作並不局限於老師,雖然學歷不高,但是英語資歷深,偶爾也會給人做做翻譯工作什麼的,忙起來的時候也是真忙。
但那裡畢竟是他的家鄉,快大半年沒回去,心裡也早已惦念不已。
而正好溫槿的生日也只剩下一個星期了。
許溪舟自然答應他,上飛機前還給空乘人員打了招呼。將近一個多小時的路程,溫槿睡了一覺醒來了,許溪舟卻始終沒敢閉眼。
飛機降落在南城,兩人又絲毫沒有停留的上了紀端特意派人給他們開過來的車,打算自駕回宜縣。走高的話來回也就三四個小時。
這會兒許父許母還在宜縣玩,玩了半個多月,玩的溫母都捨不得放人了。
溫母年輕時性子極好,溫柔,但是不善與人交談,後來再婚之後脾氣開始變壞,卻仍然不善與人交往。不然也不會和陳寅結婚那麼多年孩子都八九歲了才開始敞開心扉解開心結。
好在許母的性格恰恰相反,還偏偏就能和溫母對上話,兩人現在好的跟親姐妹的似的。
至於陳寅和許父,那也算是……其樂融融?
這兩人一個嘴笨,一個不健談,所處的圈子更是相差甚遠,基本沒什麼共同話題。但驚喜的是,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愛好:釣魚。
在釣魚上兩位老父親幼稚的像是小學時比賽跑的小孩,每次釣完回來都要數一數誰的比較多,少的就得洗碗。
倒也樂此不疲。
許溪舟和溫槿到家時四個人全都不在家。
溫母和許母去和村里其他阿姨打麻將了,許父陳寅自然是打著傘提著桶拿著杆釣魚去了。
兩個大齡男青年就這麼被冷漠無情的扔在了家裡。
兩人無奈至極,只好自己拿鑰匙開門,滄桑的回房間整理東西,然後做好飯,等著四位祖宗玩夠了回家來。
幾年前蓋房的時候許溪舟請了幾個園丁在房子前院兩旁種了一排木槿花。
如今夏日已至,烈陽盛日,木槿花叢也艷麗緊簇,芳華無暇。
溫槿房間的陽台正對著院裡,這裡地市低平,樹木茂盛。一眼望去,萬物更,一碧萬頃。
以前在一起時他們每年都會回宜縣,這次來,好像又接上了以前的日子。
像是中間兩年的分離,那些傷痛都不存在。
山野里的花是香的,草是翠的,溪水清澈見底。夜幕降臨時明月皎潔,繁星滿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