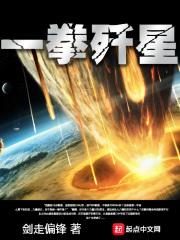言情小说>花间令上官芷扮演者 > 采薇坠楼虚惊一场(第2页)
采薇坠楼虚惊一场(第2页)
潘樾睇眼而视:“如果蔡升真的要杀我们,他有的是机会动手,不必假借由头把事闹大。”
上官芷目视仔细聆听,“应该是我们在进入生死坊之前,就已经被人盯上了。”
他推测:“他们暗中找机会在张家口借刀杀人,如果蔡升不是他们的人,我们就还有机会。”
她听得一愣一愣,不是很清晰,又微微蹙起了眉头,凑近卓澜江耳旁呢喃细语:“你不是银雨楼少班主吗?何不将身份说出?”
“银雨楼乃四大宗族之首,可听过银雨罩禾阳?”卓澜江目视她,小声道,“倘若再次坦白身份,多的是麻烦。”
潘樾垂眸若有所思,未曾听闻二人谈话,睇眼至门边大喊:“蔡坊主。”
“动手之前,能否谈谈?”蔡升扬首目视。
随后千疮百孔上面还插着两支箭鞘的木门被拉开,眸光映衬着一人的身影,便是潘樾。
潘樾赌了一把,楼下楼上人数还是他们占优势,虎视眈眈而视,蔡升正摩挲着手指,眯着眼睛抬眸掂量。
见状,他身侧一手下步至身侧,呢喃细语道:“坊主,他就是潘樾。”
蔡升冷冷笑着,脸上的刀疤令人发指,半晌后才轻启唇:“我还说谁不知死活呢,但就是算你是皇帝老子。”
“闯我的地盘,杀我的人。”他抬手指着一侧,语气拙劣,底气十足,“你也得死。”
潘樾将手拂于身后,面露悦色,悠然接茬儿道:“在和禾阳开赌坊,我作为县令,来此。”
他故意强调着,嘴角的笑容一丝不苟:“怎么能算闯呢?况且,我只赌钱,不曾杀人。”
“不曾杀人?”蔡升黑着脸盯视着楼上的潘樾,摆了摆头,意有所指,“看来潘大人也是一个敢做不敢当的人。”
他的意思,是最宠爱的妾被杀了。
“你是引颈受戮?”他不眨眼心中被怒气所遮掩,“还是跪地求饶?”
潘樾俯视而下脸上闪过一丝言笑自若:“我曾听闻蔡坊主本是逃奴。”
蔡升闻言脸色微变,不自觉摩挲着指戒,听他直言不讳:“进虎狮笼与数十人逃杀,搏命一赌。”
“最终撑着一口气,活着离开那儿,不仅获得了自由,还大赚了一笔。”
“你靠赌发家,买下生死坊,成了在禾阳除了银雨楼之外,最有权势之人,蔡坊主。”他朝前走了一步,“我说的可对?”
“潘大人不是来赌钱的吗?”蔡升停顿片刻,尚有一丝察觉,摩挲着骨节分明的手抬眸注视楼上,“怎么还做起调查来了?我和潘大人人不一样,我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我是贱命,我自己的脸面我自己挣。”
话毕,潘樾笑出了声,抬起腿才在门阶上一手抵着膝盖:“我也想学一下蔡坊主,压上我自己的命,与你赌上一局。”
此时,楼下蔡升嘴角终于露出一丝微笑,兴复不浅津津乐道:“赌什么?”
“若我今日失手被擒,无论生死皆是我,咎由自取与你无关。”屋内上官芷与卓澜江躲在角落距离甚近,近在咫尺,四目相对之下她狐疑看去,他眼神躲闪,“但是我可以活着离开。”
蔡升迎上他的目光,不屑道:“你还想怎样?”
潘樾道:“我要你生死坊从此以后,不再以人命设赌,安分守己,不再与县衙作对。”
闻言,蔡升笑的合不拢嘴,仿佛听了个笑话般哈哈大笑,抬手抵着嘴角两侧,笑后脸上又不着痕迹地沉下目光投去:“好,既然潘大人想换一种死法,那我们就赌。”
“一注香的时间,留给你写遗书。”上官芷与卓澜江于屋内观望潘樾与他谈论,“一炷香之后,赌局开始。”
屋内,潘樾平摊白纸于桌面上,随后拿起一侧的笔蘸着墨水,上官芷见状十分不解:“樾哥哥,你真写遗书啊?”
他睇眸而去未曾理会,自顾自提笔手绘,上官芷同卓澜江扭头看去,竟是生死坊的建筑屋下架屋,不免令她忍不住夸赞:“原来你早就做好准备了啊?!”
潘樾冷淡道:“我可不像你,什么都没准备就敢硬闯。”
真行,一句话就把我得罪了。
变着法说我呢,这是。
“此言差矣。”卓澜江有不同见解,“上官小姐也算是足智多谋,依我看,这便是准备。”
闻言,上官芷脸色露出一丝雀跃又含蓄莞尔一笑,摆了摆手:“哪里,哪里,不过尔尔。”
“夸你一句就上天了。”潘樾一针见血。
上官芷脸色立马沉了下来。
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