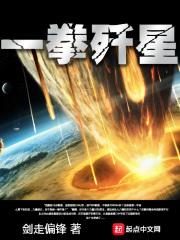言情小说>瞎夫相命免费阅读 > 第103章 情浓欲浓(第2页)
第103章 情浓欲浓(第2页)
屋门紧锁,无风吹动,房中的铃兰全都是安安静静的不见丝毫摆动,唯一摇曳不止的只有那张木制圆桌,幅度时大时小,最强烈的时候踢到边上的椅子,将椅子上的糖豆盒子都打落了下去,撒了满地的糖。
宋涟舟白衣齐整,动的欲再大也好似没乱他分毫。
唯一与之前不同的,只唇边沾染了血迹,仿佛嗜过血一般,与那一身的纯白形成强烈的反差,嗜血与纯净相结合,可怖又迷人。
沈枝熹的面颊,白中透着红。
虚弱与热烈在身体中相互交织,被迫着去感受,一次又一次的被迫着被逼到感官的最顶端。
胸口的伤处,鲜血溢出仿佛绽放的玫瑰。
浓烈的铃兰花香气,将两人深深缠绕包裹,香气前所未有的浓郁,如同这静谧的花房也是第一次这般热闹。
低语,软不成声的嗔骂,求饶,啜泣……
关着门,隔着个院子,什么也传不出去,所有的秘密,所有的禁忌之举,只落在满屋的铃兰花眼里,铃兰无声,只记在心里。
午后进的门,出来时快到黄昏。
沈枝熹被抱在宋涟舟怀里,丝乱,衣裳也乱,像是随便被套上的。
她被抱着去了正院,宋涟舟的房内。
一路上都没什么人,偶尔碰着个下人也是家丁打扮,没见着一个丫鬟女使,那家丁看到宋涟舟抱着人,也是很识相的把头低下去不敢多看。
她被放在宋涟舟的床上,他的床铺也是沉闷灰暗的颜色,跟他往日穿的黑色一样。
宋涟舟再要去褪她的衣服,她虚掩着眼皮喘息道:“疼。”
今日这一遭,比当年任何一次都疼。
比圆房之夜都疼。
“你当我要做什么?”宋涟舟将她的衣服扯下至肩头,露出受伤的伤口,接着回身去找了一瓶药回来,捏着药瓶往伤口上撒着粉末。
“这身子太弱,着实没有滋味。”
听着,沈枝熹虚虚笑。
没有滋味,还折腾了那么久?
“过会送你回去,我们明日,再继续。”
宋涟舟没有多留,给她上过药就转身出门去了,整个人都泛着一股生疏的冷情,走的是毫不留恋。
自然,沈枝熹也乐的一个清净。
静下后,虚弱之气也慢慢浮了上来,眼皮打架抵不住困意。
屋外。
卫鸿手中拿着一卷白纸进了院子,将东西递给宋涟舟说:“公子,这是皇后娘娘近三年来的脉案,我们的人偷偷抄录的,再远一些藏得深不容易得到。”
宋涟舟接了卷纸,摊开来看。
从脉案上来看,没看出什么特殊的。
“能拿到手的未必就是真的,昨日刚事,太医院这几日的防备也肯定会加强,不可操之过急,免得露了马脚。”
“公子放心,这一份脉案是在皇后娘娘病前几日就抄录好的,公子一直嘱咐务必多盯着些,所以每次太医去给皇后娘娘诊完脉之后,我们的人也都会时刻在这份抄录的脉案上记上一笔。独独昨日的脉案还未来得及去翻看,如公子所说,若娘娘的病另有意外,这几日定是最要紧的关头,我们的人也不敢鲁莽行事。”
“嗯。”
宋涟舟淡淡回应,片刻后却拧了眉。
“脉案上说,皇后多日前就已经出现了呕吐不适的症状。”
“是的公子,不过这并不是娘娘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这些年一直都有反复的出现这种状况,有时还会头晕眼花,开了几副药喝下后,症状又会消失,看着就只是普通的身体不适,就如太医所说,是常年忧思又是旧伤未愈留下的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