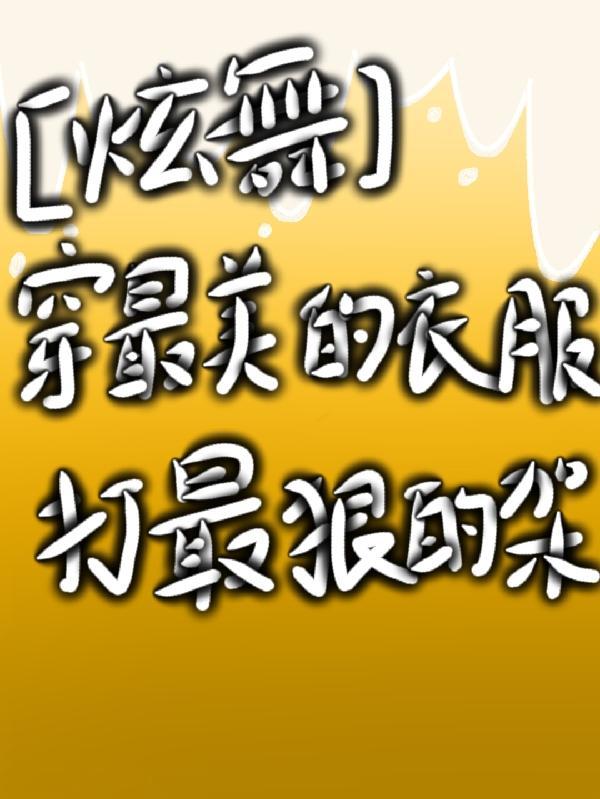言情小说>独行者剧目 > 第49页(第2页)
第49页(第2页)
立秋早过了,枯黄的气息盈满天地。
帝克斯的二头目又开始执行任务,辛勤地为帝克斯开疆辟土,言行并不见得有何异常。
无事可做的夜里他常自己一人,抱着酒坛子去屋顶吹风。寒风呼啦啦一过,便总有种负伤的孤狼夜里在山顶上嘶嚎般的苍凉悲壮之感——虽然风吹得头发衣角凌乱,旁人远远见着像屋顶镇宅的鬼怪石雕,并不见得有多帅气。
微醺的时候,摸着那块海星石,自然还是会去想那妖孽。
其实是他先前错了,和行过一起的那些日子里,也并不全是苦情——若和一人在一起,感受到的只有求不得的悲哀与痛苦,又如何会爱得上。
见着那人,最多的还是欢喜。见不到那人,思念虽刻骨地痛,但回忆里总有他不肯拉下面子去承认的甜蜜。
而行过……那些与他一起喝酒聊天、争闹打斗的日子里,行过开开心心的笑容,哪里能是假的。每次被行过所救,醒时等在床边那双眼里的关切,又哪里能是假的。甚至连那日里激情缠绵之后,行过仰起脸来问他是否真的喜欢自己,得到肯定的回答以后,眼里流露出的高兴,也不是假的。
行过自己也承认说,与他在一起的日子,是有开心。
他不是自恋,但总也会想,行过也许对他是特别的,也许对他的感觉是与旁人不同的,只是这种浅浅淡淡的喜欢,还不是爱,还不够填补心里的空,连行过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他们纠纠缠缠、挣挣扎扎这三年多来,行过救过他数次,悉心地照料他数次,二话不说地帮了他数次,甚至连走之前,也嘱咐其若日后要帮着他……
而他帮过行过什么?给过行过什么?
明明心里喜欢,表面上却总装得冷冷漠漠,与行过说话时态度总是冷硬,硬要他陪自己做这做那;就算最终亲口说了我喜欢你,接下来也不过是丝毫不怜香惜玉地纵欲一场、将对方弄得伤痕累累、血迹淋淋……
他不顾行过的感受,硬要将他封印,将他强留在自己身边,行过也没有怪责他,没有再来找他的麻烦——即使那不再来找麻烦的理由也许是急着去见那女子、与她化而为一。
除了没将他放在心上,除了爱,行过什么也不欠他。
而谁又规定了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另一个人就非要爱回去?
所以他落到如今地步,只能是活该。他独自一人守着这无边的寂寞,想着那个也许早与和别人化为一体、不再存在于这世上的人,也只能是活该。
数月后北迟国那边来了消息,老国王传位于王储,不日病殒。北迟国举国大丧一月,接着便是新王登基。
然而就在新王的登基大典上,一枚从暗处来的飞镖,当着跪拜百官的面,正入新王的额头,血溅王座。
凶手是必须要搜查的,但国家大事也一刻不能耽搁,于是两个王的丧礼一起举行,登基大典推迟数日再举行,这一次的新王自然是王储大公子肖谛。
这些事披三少都只是听闻,与北迟国的事务首领交于麒麟前去处理,并无他再插手的余地。他此时……正从两个任务的夹缝间抽出了时间,暂时断了与帝克斯的联系,赶往玲珑国。
他想去看一看。
即便……那个人不是“行过”也罢。
“下曲姝河谷?!”
酒店小二瞪圆了他的眼睛。
“客倌,您不要命了?这河谷两边都是悬崖峭壁,连下去的路也没有,又传说有凶兽出没,您这可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啊!”
披三少憔悴得一点也不像肉包子、只最多有点像菜包子的脸上半点表情也无。
“老大魔障了……老大魔障了……”仑昆缩在酒店角落里的另张桌子边上抹眼泪。
“老大上次与行哥就是在这里分开的……行哥难道是河谷里的狐狸变的?”昆仑皱着眉思考着。
“那行哥难道是……”仑昆恍然大悟地接了一句,“……河狸精??”
昆仑一个哆嗦,就着手里筷子往他老弟头上狠狠一敲,“放屁!咱嫂子能是那么小小胖胖的东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