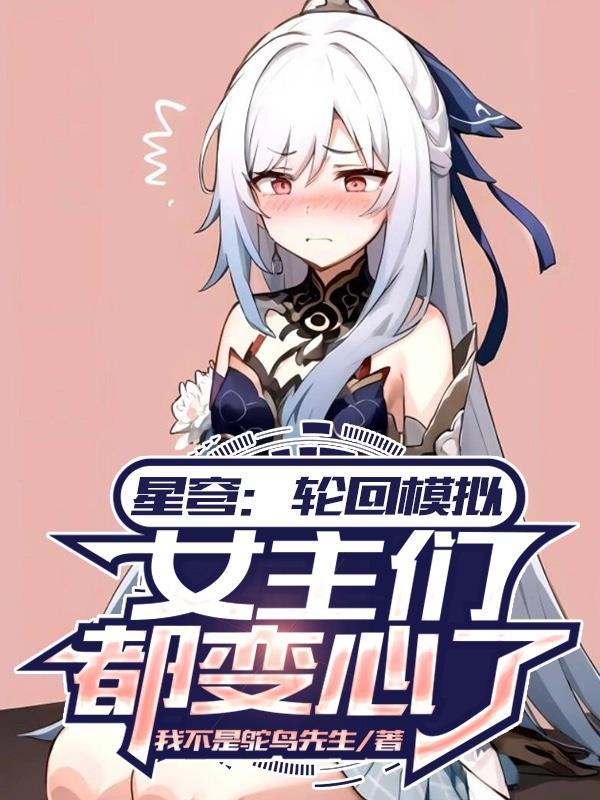言情小说>豪门劫薄情总裁的契约情人 > 第70页(第2页)
第70页(第2页)
杜云起身倒了一杯水走过来递给步若痕:“喝口水放松一下。”
步若痕接过水杯一口饮尽,舒出压抑在胸口的那股气:“行歌,我先派人去救唯律,他伤得很重,他现在……”
风行歌拨了一通电话按步若痕说的地方让人去找然后秘密送到风煌医院,千万不能让媒体钻风。
“云,你先回医院吧,唯律就交给你了。”风行歌收好电话别人深意地看了杜云一眼。
杜云淡笑起身抬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倾身在他的耳边低诉:“行歌,掌握分寸,她现在身体很虚弱。”
然后杜云越过风行歌离开了,一室的安静只留给了两人。
风行歌坐到白色的靠椅内,神色轻松,唇角带笑:“昨天你去哪儿了?为什么一夜不归?”
“我去了我爸的墓地。”步若痕半坐着,背靠在柔软的羽枕上。
“一个人?”风行歌修长的十指交握,左眉轻挑,明显地质疑。
“唯律跟着我去了那里,然后我们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谁,你知道吗?”步若痕抬眸看向他,有些冷漠,“想知道我和唯律的事情是吗?我们现在这个样子都是你害的。”
风行歌的眸子逝去了明亮的星芒,暗沉幽静,好看的薄唇也紧抿成了一条线,那样刚硬。
“上次在酒吧你打得那几个人报复的手段和你当初残忍的方式有过之不及。唯律为了保护我而被他们打成了重伤,幸好我们上了车,开车逃走了结果唯律却中途昏迷了,我的东西全在我母亲家里。我一个走了这么久的路回来就是希望你能看在唯律是你的亲弟弟的份上救救他,而我没有什么要说的。”
“什么意思?”风行歌听得心中越发悲凉,“你认为我真会为了你而误会唯律,对他采取什么手段?”
“你心里应该明白。”步若痕低头一笑,“是,也许我真的没那么重要,也许我把自己想像得太高贵,忘了我只是步家在你这里一低债的东西。”
“步若痕,你非得像一个刺猬一样吗?”风行歌咬着牙,这女人真是不知道好歹,“你在家里休息我要去上班了。”
“我要去医院看唯律。”步若痕正掀开被子跳下了床。
风行歌一把按住她倒在床上,两人姿势暧昧:“你--哪儿也不许去。”
“你放开我,他是为我受伤的,我要去看他天经地义。我再不想忍受这样的生活了。风行歌,这一次我绝不心软了,我不会和你结婚了,要结你去找步林惜。”步若痕瞪着他,大吼了出来,“如果不是你我的人生不会面目全非,我的亲情我的爱情就不会毁灭……如果不是唯律出事了我绝对不会回来……”
步若痕说着说着眼睛上又漫了水气,可是她硬生生在将它们全数逼了回去,看着她如此决绝的模样风行歌的心像是被剜了一刀,痛苦至极。
步若痕一口咬上了风行歌的手腕,狠狠地咬上,直到她的口是漫延开了血腥味,他都不曾松开手。步若痕竟不忍再用力,心上也是难过悲凄,那是一种让她深深无力和无法逃开的无形的力量。
“从今天起你哪儿也不能去。”风行歌慢慢松开了手,心已经冻结成冰,片片风化。
是什么让相爱的人如此折磨如此悲伤?让相近的恋人仿佛隔着两个世界?
“如果你不要去看他那么我就从这里跳下去。”步若痕快跑到往落地窗外的露台而去,一脸决绝,“现在我只有一个人了,一了百了。”
亲情没有了,爱情变质了,她只是一片浮萍,不畏生死。
风行歌与她对峙着,目光冰冷的可以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