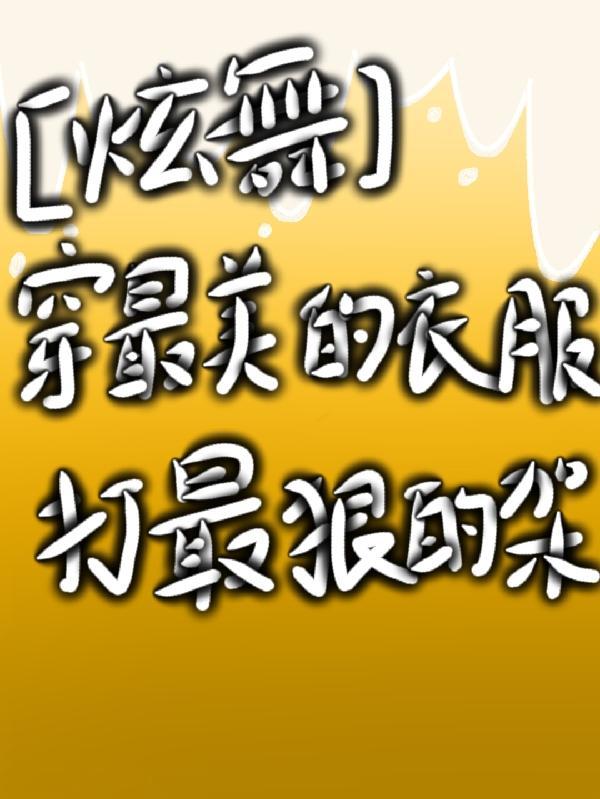言情小说>直线下坠剧透 > 第53页(第1页)
第53页(第1页)
今天见到你哥哥了,他成了我的医生,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医生。姑且把他当成医生吧。我向他提起了飞儿,一下子痛哭失声。他没有表现出来认识你的样子,我真的很奇怪,不知道他为什麽来,不一定是来找我,也许是来恨我的。
和宋宁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两个男人住在一起,他想要,我还没想好给不给,也许真的是我的心理障碍太强,说白了,我是真的有点害怕,以前是怕我没法全心全意的爱他,我害怕我所在的这个圈子,现在,我怕把他拖累了。
飞儿,如果你哥哥是来恨我的,我该怎麽办?
7月6日
飞儿,离上次给你留言竟过去了快两年。本来不想用我的声音打破你日记原有的格局,这是你给我的,一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所有的声音都在这里。是你让我知道了爱和怎样去爱一个人。我找到了你当时爱我的感觉,想过来告诉你,飞儿,认识你真好。
如果有可能,我们会到西藏陪著你。
後记
七个月後,等我办妥了繁杂的手续,我和梁恺去了美国,我不知道梁恺是怎麽跟飞儿父母说的。飞儿的母亲谢谢我在中国对飞儿照顾,那种感觉就好像他们知道了什麽似的,後来我知道不是,因为飞儿母亲说那都是她从飞儿的日记里看来的,说飞儿的日记里写了很多我的事,怎麽在他初到中国时给他找住的地方,陪他玩,陪他去了哪些地方,弄得我都胡涂了。後来我终於明白那是梁恺写了几本日记给了飞儿的父母,至於笔迹像不像和他们为什麽没看出来,我想梁恺一定用了很多心,所以我没有问他。
飞儿的母亲和飞儿长得很像,他父亲拿了飞儿的很多奖杯给我看,还有从小到大的照片。那一天,我待在飞儿家就像待在地狱,那是一对失去了优秀儿子沈痛的父母,他们的每一句回记敲在心里就像刀子剜著我的心。可怜的飞儿,那个善良的纯粹的让我永远忘不了的飞儿,短短的二十一年,静静的来了,又静静地走了。
梁恺的父母对我还算客气,当然是那种你能感觉的出来的客气。我没有被他们家的气派吓住,多少房,多少车,吃饭怎麽个讲究法,现在已经没什麽能吓得住我的了,我的精神早在梁恺的锻炼下百炼成钢坚硬如铁。
去了我才知道除了一个妹妹,梁恺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掌管著他们家族的生意,这也是他们能最後能容忍梁恺去做医生还找个男人结婚的原因。
我和梁恺注册的时候,连他父母也没来参加,据梁恺说是为了他们家在华人中可爱的面子。既然老丈人丈母娘要面子,我大度当然得给全了他们的面子。所以,除了肖锐,还有特意赶来的明哥和向雷,加上梁恺总共有七个人,我们俩在那里互换了戒指,是那种普普通通没宝石没钻石的东西,是我们俩挑了三家才挑出来的东西。然後我就拿著戴了戒指的手得意地在肖锐面前晃啊晃,晃出了他的眼泪,梁恺直接给了我一巴掌,我才收了手。
明哥和向雷当然是柳暗花明了,向雷继续在公司里冲锋献阵,明哥坐阵大後方出谋划策,大有夫唱夫随的架势。
我家里这边当然只有蓝翔一个人知道,他毕业後签了一家外企,还要海绵里挤时间去远游,sida不甘寂寞终於甩了这个小阿三另攀高枝去了,蓝翔只痛苦了三天,就又恢复了常态活得生龙活虎。知道我去美国注册光要我给他买的东西就列了一大张纸,末了,拿了一个不知哪里捡来的木头脸谱算是给我的贺礼就把我打发了。
在去美国前,梁恺跟我去看了一次妈妈。他是以我合夥人的身份去的,妈妈一点也没怀疑,收著梁恺买给她贵重的礼物,一个劲儿的让梁恺多照顾我,说我从小就任性,认死理,脾气还死臭,总之,把我贬得一无事处,弄得我坐梁恺旁边真好像一个还没长大的傻孩子。妈妈和继父和我们俩一起吃了一顿饭。在那个饭桌上,我第一次叫了那个朴实的老教师一声爸爸,看到妈妈一脸欣喜,我也挺高兴。
和梁恺注册之後,在美国那个老资社会里我只呆了一个月,然後和梁恺回了国,因为我不会说英语。如果你想买瓶自己喜欢的啤酒还要带个翻译的话,任谁多一天也在这个不待见你的地方待不下去,更何况梁恺那兔崽子还爱用鸟语在床上打击我,弄得我回回以为自己就是那个难看的gv男猪角。
回了国我们卖了梁恺的那套200平方的大房子,还有那个10楼的小两室,只留下了我的那套,因为梁恺说那房子以後还会升值,要留就留最值钱的。我一听就两眼冒星星指望著这房子能再撑上三十年让我成一个暴富的小老头。
我们商量过在哪定居以及以後的生活。梁恺说听我的。
我说要不去西藏吧,梁恺爽快的答应了,我掐著他的脸问他是不是还爱著飞儿,他说当然,飞儿是永远的飞儿,在他心尖子里藏著,不过蓝天现在是他的老板,他得挖肝掏肺捧著。
我当然喜欢当老板。
然後我们去了西藏。早在我第一次去西藏时就迷上了这个地方,比飞儿还甚,那里有灿烂的阳光和纯朴的民风,天蓝水清,只要我的哮喘不折磨的我离开,我真的愿意一直生活在那里。
梁恺继续做他医生,我则开了一家户外用品店,做了一个真正的小老板。偶而我会和梁恺去k歌,像个真正的大明星一样享受著众人瞩目的目光,那时候最得意的不是我,是梁恺,还白痴的给我献过花。
我的生意只能算一般,除掉了房租和杂七杂八的费用,刚够生活。每次梁恺问我,那种滑翔器那麽贵,一年也卖不了几个,为什麽还要进,为什麽每天还要扛进扛出的穷折腾,我就诋毁他说他就见不了我卖一个抵得上他干一年。其实梁恺干一年真不如我卖一个挣得多,他看病大多不要钱,搭药搭房子有时候还得搭上我给他当护士,和他的假模假式的高尚相比,我是一个真正的奸商,成天为了蝇头小利和人吵得不益乐乎。
我不吵不行,因为我们得靠这个吃饭,因为当初说好了,在西藏,我们就得自己努力打拼,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我们都没法像个老太爷拿著手里的钞票舒服过日子。
在西藏差不多一年後的一个晚上,我们坐在院子里乘凉,稍带看看星星月亮,我突然唱起了‘雪绒花’,梁恺的声音也加了进来,唱完歌後,不知怎麽的,我谈起了飞儿,谈我们第一次认识,他弹的那首‘海上钢琴师’,谈我们去过的日喀则,谈我们捡的那块黑石,谈飞儿後来喜欢的滑翔,谈我送飞儿的三件礼物,水晶球、石头和滑翔伞;飞儿送我的三件东西,第一教我识谱,第二是那套房子,第三是那几本日记,然後我问梁恺,晚上睡不著觉的时候,想著那个不知道内容的日记,想著那个不知什麽原因的跳楼,心里难受不难受,胸口堵著一块大石头的时候,憋气不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