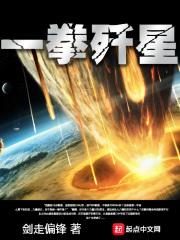言情小说>盛夏怪兽简介 > 第61頁(第2页)
第61頁(第2页)
&1dquo;卓越你什麼時候這麼天真了?”我笑,&1dquo;這是出櫃啊!還不如出軌呢。”
他被我逗笑了。
這種時候我才突然發現,我哥的笑聲其實真的很好聽。
在異國他鄉,我們好像跟很多事情都和解了。
最後,我還是答應了去他家過年,甚至還很老土的在上門前買了年禮物。
卓越和他那個外國男友住在一起,在距離我的住處稍微有點遠的公寓裡。
那個春節我們誰都沒有提起余柏言,就好像在我們的世界裡從沒出現過那個人。
可是除夕一過,大年初一的早晨,我在他家的沙發上醒來。
睜眼的第一反應是:如果余柏言在就好了。
卓越問我打算什麼時候回國,問我要不要在某個休息的假期去一趟舊金山。
我全部搖頭回應。
我不知道怎麼辦,於是一直逃避著。
後來我才知道,我膽小如鼠地躲在都柏林那幾年,余柏言在舊金山苦苦掙扎著。
他讀博遭遇瓶頸,論文屢屢被斃。
我們分開前他就已經重度焦慮症,在和我斷了聯繫後,一度重度抑鬱。
那些事都是很後來他才告訴我的。
我也是那個時候才知道他媽媽為什麼突然去了美國。
是他在用最後一絲求生欲在向她求救。
我問過他為什麼不告訴我。
他的回答是:&1dquo;不知道,當時就是怎麼都說不出口。就像你也有很多事不想讓我知道。”
他說,他不想讓我覺得他是個廢物。
可他余柏言怎麼會是廢物呢?沒有他的我才是真廢物。
但那都是後來的事了,我在都柏林沉浸在自己的憂鬱中,做作矯情,苟延殘喘。
我就那麼在愛爾蘭混了三年,混到我一腳踩在了三十歲的門檻上。
上大學那會兒我還跟余柏言開過玩笑,說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三十歲。
理由是他干我幹得太狠了,說不定哪天就死在他身下了。
那時候他從我指尖搶走我的煙,抽了一口笑著說:&1dquo;少胡說八道,你三十大壽哥給你大擺宴席,好好慶祝。”
我們也真的親密無間過。
可我真的到三十歲了,余柏言都不知道在哪裡。
我三十歲生日那天,陪我度過的是當年余柏言上大學前送我的綠色小怪獸玩偶。
那個丑東西竟然一直跟著我從家鄉到了北京,又來了都柏林。
我說它丑,余柏言卻非說像我。
因為這事兒,我沒少打他。
可當他不在,他送我的丑東西成了我唯一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