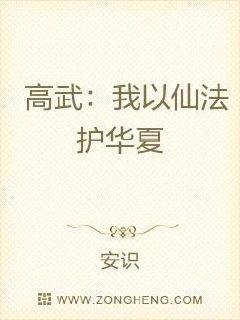言情小说>驯养无弹窗 > 第525章 杀了他吧(第2页)
第525章 杀了他吧(第2页)
霍危瞧着那,眸光染上一层血色。
她什么时候变这么坏的。
跟谁学的?!
任清歌慢慢悠悠地应付他,“看样子还是不甘心啊,没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霍危饱受折磨,妥协,“知道错了。”
“知道错了你不好好受罚。”
霍危纠结了半响,才说出那个字眼。
任清歌听得耳朵嗡嗡的。
她腰眼麻了一下,把腿放下来,用裙子遮住。
“几次?”
霍危又沉默了。
仿佛多得数不清。
任清歌轻嗤,“霍秘书,你在会议室冲你那群下属火的时候,他们知道你这么坏吗?”
霍危脑子白,再也没有了任何想法。
只有一句,“老婆,你放过我。”
任清歌起身,走到他跟前。
霍危身处崩溃边缘,赤红着眼呢喃,“清歌。”
任清歌被他这幅模样勾得有点软,但她撑得住,轻声问,“是不是好难受?”
“嗯。”霍危哀求,“帮帮我。”
任清歌可记仇了,“有一年暑假,你去监狱里实习勘查。”
霍危,“……”
啊,杀了他吧。
杀了他。
任清歌的手描绘他的眉眼,他的唇,再是他的胸膛。
“你上次威胁我的时候,怎么说的来着。”任清歌在他耳边吐气,“折磨犯人最好的办法就是,给看不给吃,是吗?”
手指,落在某个地方。
霍危急切地吻她,可刚碰到就被她躲开。
他气息乱成一团,“清歌,上次我给你了,你不能这么对我。”
任清歌笑得像一只偷了腥的狐狸,“可我坏啊。”
话说完,毫不犹豫的转身走了。
霍危绝望至极,“老婆……”
任清歌走向衣帽间,收拾了几件衣服。
“我走了,这段时间我住在阿音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