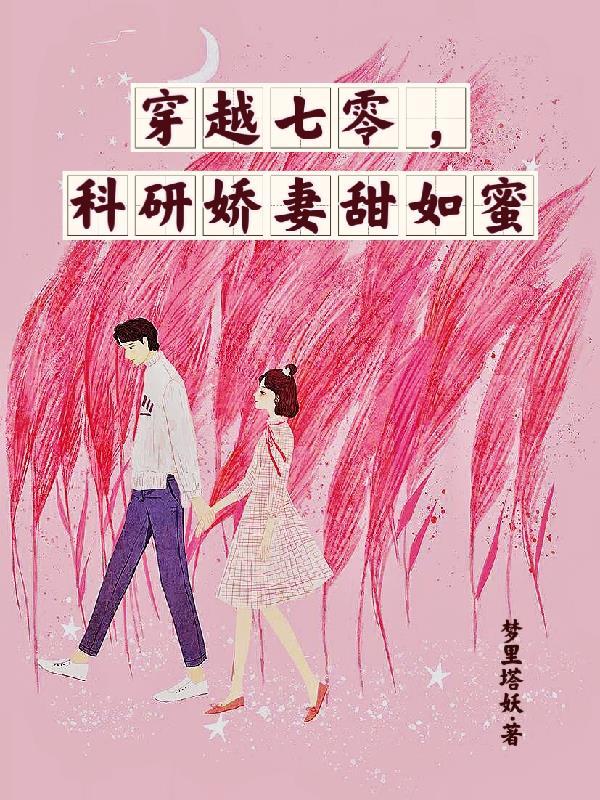言情小说>战争的演变游戏 > 第九十三章 来访者(第3页)
第九十三章 来访者(第3页)
“这位。。。。亭长。”
驿站里的人正在工作。
一个男人领着十几个精壮的小伙子在仓房里整理蜂窝煤,听见禽理矩的话,连连摇头:
“我可不是什么亭长,我就是个站长。”
“你们是从外面来投奔我们的吧?”
“是,我们从燕国来。”
“那行,跟我来登记吧。”
男人脱掉手套,擦了擦粘着煤灰的手臂:“没什么问题的话会有人把你们用列车带走。”
“我可警告你们,到地方别生事啊,遇上事找衙门。”
跟着去登记的他们看见了铁路。
确实是两根地上的金属杆子,以横放的许多保持间隔的木方和碎石子为基,延伸到极远处,头尾不见尽头。
“。。。。。。”
他们感觉到了萌芽的工业力量对三观的冲击。
这么大规模地运用金属对他们来说是超乎想象的。
“站长。”
禽理矩稳住心神,问男人:
“您说登记,您读过书,认识字?”
“我上过夜校,认全了字,书看得不多,也就看过那么几部。”
“夜校?”
“就是每天收工以后有人领着我们认字识数。”
又一项对三观的冲击。
他们当场怔住,禽理矩霎时间汗毛炸起,一股热血直冲脑门。
他听到自己的声音发颤:
“你们那里能上夜校认字的人,多么?”
男人回过头。
脸上写满了理所当然:
“所有做工的人和小孩儿都要学认字识数,还要学一样乐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