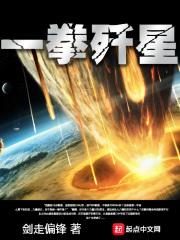言情小说>学神同桌总想撩我笔趣阁 > 第57頁(第1页)
第57頁(第1页)
時綏僵著臉瞅了半天自己的書包,餘光瞥見6淮知蒼白的臉色,煩躁地抿了抿唇,將書包拉鏈拉開,把校服塞進了6淮知懷裡。
「還你。」時綏說,「穿上。」
6淮知就只有這一件外套嗎?冷了不會說?
在風裡挨凍給誰看呢!
6淮知看著懷裡的外套,有些詫異地抬頭看向時綏,時綏則是不自在地別過了臉。
6淮知很淺地彎了一下嘴角,「謝謝。」
6淮知人生的好看,只不過平日不說話的樣子稍顯冷淡,可笑起來的時候那種感覺一下散了,像是冰雪融化,化成涓涓細流,溫潤無聲。
時綏的冷臉都在他這笑下有些維持不住,本來想說,這就是他自個的校服,謝個屁。
可看到對方嘴角那抹弧度,嘴邊的狠話又咽了回去。
「你們繼續歇著,我再下去跑會兒。」時綏說完往台階下走。
眼不見心靜。
可汪城一把拉住他,「不是,哥,你不緩緩的啊?」
他被卷的累死了。
要不是操場人不少,他都想直接在看台上趴著。
時綏木著臉:「我不累。」
汪城:「……」
旁邊的池青都看不下去,「時綏,你精力是不是太旺盛了點?」
雖說時綏之前也很能跑,可最近這體力消耗程度卻有點反常,每次都是跑到實在撐不下去,坐在操場上汗滴如雨,大口劇烈喘氣才罷休。
汪城聞言愣了愣,仔細回想了一下,心裡一咯噔。
時綏狀態真的有點不對。
「爹,你最近沒事吧?」汪城問。
時綏避開了他的目光,「能有什麼事。」
有點手癢而已。
最近半個月都沒有人來找他約架,昨天陳牛他們也不頂用,放了幾句狠話就跑了。
時綏說不出心裡那種感受,像是某種情緒到達臨界值,卻怎麼都沖不破那層束縛。
他只能藉由放學後去操場跑步,發泄多餘的精力。
汪城哪裡沒看出時綏的迴避,暗道不妙,不過面上沒有表現出來,笑呵呵地拍了拍時綏的肩,「你不是跟學霸都還感冒著呢嗎?要不你們倆在教室學習?我跟池青練就行了,反正你們又沒項目。」
「再說,你不是這次月考要考進前年級前四百?」
他自小跟時綏一起長大,能隱約感受到時綏的狀態,情緒積壓在一起,卻被時綏強制壓下去。
特別是當時綏發呆或者默默無言的時候,那種感覺最為明顯。
像是火山爆發前的寧靜。
之前也有過這麼一段時期,那時候時綏狠狠跟人打了一架,不要命似的,差點把自己打進醫院。
這是個非常不好的前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