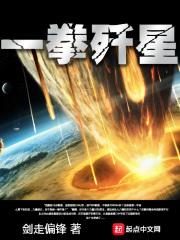言情小说>昭昭天明txt > 第143頁(第1页)
第143頁(第1页)
穿過橫越小河的小板橋,柳七和沈忘便踏上了篦子巷的路面。一路上,柳七多次要求給沈忘把脈,都被他橫欄著豎擋著,說什麼也不依,到最後竟是連「男女授受不親」的訓誡都搬了出來,讓柳七又好氣又好笑。
不過,沈忘現在的身體已經是無須把脈也能明顯看?出的虛弱了,一路上他幾乎是走一陣便要歇一陣,行在板橋上更是晃晃悠悠,腳步虛浮,柳七隻能用力拽著他的袖子,謹防他一不小心摔下河去。
終於在日落之前?,二人到達了篦子巷的最深處,幾乎是一眼便將魯盡忠的宅院認了出來。它同自己?的主人一樣?,歪斜著身子,矗立在一眾平整簇的瓦房之間。細看?它的牆面,竟不僅僅是磚石壘砌,還混雜著貝殼和碎石子。很難想?象,在這樣?商鋪眾多的城中心,還會有這樣?窮困潦倒的人家。
小瓦房的門是竹子編的,辨不清年份,看?竹子老化的程度幾乎可算是前?朝遺物,輕輕一扣便發出喑啞的呻吟聲。為了出行方便,沈忘和柳七都是男裝打扮,沈忘更是戴上了大?帽以掩藏面容。廢舊的老宅前?突然來了兩位面容俊逸的少年郎,引得周邊的鄰里都探頭?探腦地向著這邊張望。
「你們是要找誰啊?」一位正在自家門口曬太陽的花甲老人好奇地問?道。
「老人家,我來尋一位年輕人,他叫魯盡忠。」沈忘微笑著彎起眉眼,從容不迫地說著瞎話。
「小伙子,他是欠了你的錢嗎?」一位河畔洗衣的婦人也插進了話頭?問?道。
「真讓您說准了大?嬸,在下?和舍弟此番前?來正是為討要一筆陳年舊帳,還請諸位幫忙引見。」沈忘就?坡下?驢,順嘴胡謅道。
那婦人和老人無奈對忘了一眼,皆是搖了搖頭?,嘆息道:「作?孽啊,小伙子,你這筆錢,怕是要不回?來了,趁著天色還早,快些回?吧!」
「這是為何?魯盡忠是搬家了嗎?」
老人揚起手杖,指了指那幾乎快要脫出門框的竹門:「魯家人最近算是倒了大?霉了,前?些日子,這家老太太被一幫凶神惡煞的人請走了,麼兒……也就?是魯盡忠想?攔,奈何對方人多勢眾,倒是討了一頓好打。從那時起,魯盡忠就?沒有再回?來過,他欠的糊塗帳可不算少數,這些日子裡來討債的人也有,但?都是無功而返,所以啊,我勸你們倆娃娃也快些離去吧!」
「是啊」,洗衣的婦人一副深諳內情的模樣?神秘道,「我聽說,那魯家小子犯了事,被官府捉去了,也不知何時才能出來。魯家老太太也是命苦,養了這般不成器的兒子,臨到老了,還要經受這般磋磨喲!」
「哪像吳嬸你,兒子爭氣,女兒高嫁,福氣尚在後頭?呢!」老人捋著長髯誇讚道。
洗衣的婦人樂得合不攏嘴,正欲將話題引到自家孩子身上,卻驀然發現,剛剛還仔細聆聽的兩個年輕人不知何時已經離開了,河畔只剩下?她與老者兩人。
「現在的孩子啊,人家話還沒說完,這便跑了……」婦人意猶未盡地埋怨道。
小板橋下?的河水潺潺流淌,倒映著西天火紅的夕陽,世事荏苒,白馬逐光,沒有人還在意那半掩的竹門後曾經上演著什麼樣?的悲歡離合,魯盡忠和他失蹤的老娘,就?如同橋下?河流中兩顆再普通平凡不過的水滴,被推擠著,簇擁著,湧向他們不可知的前?方。
而那妄圖以一己?之力改變整條河流流向的人,此時正頹然坐在一株兩人合抱粗的柳樹下?,用拳頭?重重地向地面上砸去。
「這幫混帳!」
沈忘已經很久沒有發這麼大?的火了,此時憤怒的烈焰正炙烤著他的心,讓無時無刻不折磨著他的眩暈感都暫時消退了。
「我本以為,這幫人為了讓我放棄追查蔣大?人的案子,指鹿為馬,掉包了蔣小姐,再反手來個殺人滅口,讓案子查無可查,這便結了。誰想?到他們還有後手,為了防止我通過冒牌蔣小姐的案子查到他們頭?上,便用魯盡忠的娘親作?為威脅,讓魯盡忠替他們擔下?了罪過。」
沈忘的眸子亮得驚人,他死?死?盯著面前?波光粼粼的河水,臉上浮起摻雜著懊悔與自嘲的笑意:「不僅如此,他們還巧妙拿捏了斷案人的心思,故意讓魯盡忠將案情說得半真半假,還留下?了上吊自盡這一突破口,讓我誤以為自己?通過推理還原覓得真兇。這齣戲,當真回?環往復,一唱三疊,而我……偏偏信了……」
沈忘簡直不敢想?象,若不是最後魯盡忠的狀態讓他生了疑,真的讓冒牌蔣小姐一案就?此結案,那潛藏於背後之人會不會就?真的無罪脫逃,接著逍遙法外了呢?
柳七雖然也是驚愕於小小一座歷城縣衙竟然盤根錯節,藏污納垢至此,但?她天性?冷靜非常,此刻又擔心沈忘虛弱的身體承受不住,便刻意引開了話題:「沈兄,你記得嗎,去蔣宅的那日我曾問?過你,這歷城縣衙上百號人手,到底有沒有可信之人,你現在有答案了嗎?」
沈忘眉頭?微蹙,思忖道:「倒是有一人,我現在還難以定性?。」
「此人是誰?」
沈忘沒有立刻回?答,而是仔細分析道:「此案進展至此,在這渾水中趟了一這麼一遭,我也算看?得分明,只要是言之鑿鑿那冒牌的瘋女子就?是蔣小姐之人,便斷然不可信。所以,將卷宗給我並介紹整個案情的汪師爺和巡邏發現屍體便一口咬定是蔣小姐的燕隋燕捕頭?,都是做局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