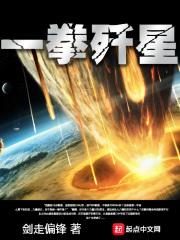言情小说>浪漫悖论txt百度 > 第53章(第2页)
第53章(第2页)
被装在一个模糊又摇晃的摄像机画面里,周围乱糟糟的,是媒体杂乱的脚步声,孔宴的手按在她羸弱又细瘦的肩膀上,笑着对着镜头说:
这可是我唯一的女儿,不管是哪一岁生日,当然都要好好过。
孔黎鸢的脸上似乎没有表情,又或者是对着画面笑了一下,是很标准很没有瑕疵的笑。
那段视频过了太久,像素变得模糊。
可付汀梨在梦里都觉得那个笑太标准。
是昏沉沉的路灯下,在墓园前被人群包裹着的孔黎鸢。
已经去世的姜曼,在十多年后突然被爆出当年生完孔黎鸢之后,有过一段长时间的产后抑郁。
当时孔黎鸢刚得了最佳新人奖,穿很普通的黑色外套,戴很普通甚至让人觉得灰暗的黑色鸭舌帽,被围堵在昏暗的街边。
而对准她的摄像头往天上抬了抬,定焦在一个石质大门前,然后又缓慢移到孔黎鸢没有什么起伏的脸上。
闪光灯快而疯狂地往下按,她微微抬起下巴,鸭舌帽下的眼隐在流淌光影中,看围在她身边越来越多的人。a无限好文,尽在晋江文学城
动作很慢很慢。
很多嘈杂疯狂的声音涌到孔黎鸢面前。
她没理会,只又有些倦懒地收回视线,戴上口罩,上半张脸隐在了昏沉沉的光影中。
跟在她周围的人那么多,但她穿一身黑,低头,快步流星地走着,却又像是那么孤立无援。
在梦里。
付汀梨默默跟着她,一步一步地往前踏着,拥挤嘈杂的人群变成了乌泱泱的水,缓慢溺到孔黎鸢的胸口。
孔黎鸢淌着黑漆漆的水,走到更阴更暗的地方。付汀梨无处可去,也跟在后面,淌着冰凉凉的水。
水一同淹到她们的下巴,湿漉漉的,憋人的,晃荡晃荡着。
她看她站在昏暗的街头,竭力抬头望一眼高高围墙,墓园里高大的树,呼出一口一口很长的气。
付汀梨猜,孔黎鸢说不准在心里想着就这么爬上去算了,爬到围墙里边,或者想坐在街头点一根烟。
但孔黎鸢没有,只是又隔着很虚无很飘渺的空气,莫名和她对望。
然后往这边不轻不重地笑一下。
于是涌在周围的水,又一下变成了乌泱泱的人。
从付汀梨的身边擦肩而过,一窝蜂地围过去,把孔黎鸢围得水泄不通。
好似沉入水底。
窒息感瞬间涌了上来。付汀梨好像也跟着溺了进去,心脏涨得很痛很痛。
“嘀”
梦里的景象倏地消散,被一声极其尖锐又极其漫长的喇叭声击得七零八落。
付汀梨觉得自己有些呼吸不过来,像是有什么东西闷在胸口似的。
而朦胧间,传到耳边的,是有些遥远又有些嘈杂的争吵声。
好像不来自于她们这辆车,而是来自于车外,隔着一层车玻璃和嘶吼着的风声,听不太清具体内容是什么。
付汀梨模模糊糊地睁开眼。
像是镜头在缓慢调整焦距,一切从模糊到清晰。车窗外是雪,飘洒摇曳的鹅毛大雪,顺着昏黄路灯飘落下来。
到北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