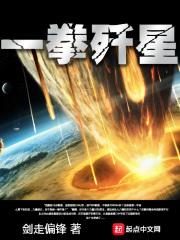言情小说>浪漫悖论全文免费阅读在线 > 第68章(第3页)
第68章(第3页)
“我拍了啊?”
她说着。然后在一段较为漫长的留白之后,听到孔黎鸢说“好了”。
然后便按下拍照键。
定格的那一瞬间,她看着照片里眉眼含情的女人,突然觉得好熟悉。
手机上跳出通知,是向导来,说找到民宿了,然后是一大段她没来得及阅读的字眼,像是“将就”“挤一下”之类的。
她没放下手机,只盯着镜头里的孔黎鸢,突然在恍惚间想起一件事。
遗忘一个人往往都是从模样开始的,最后才是声音。
尽管她没想过要强逼自己忘掉,但四年时间足以将一个只相处过三天的面容变得模糊不清,只记得一个符号或者是标记。
就算她还能把那些事情记得清清楚楚。但有时候也惊讶地现自己竟然想不起那个女人的脸。
而之所以能将孔黎鸢的眉眼记得那么清晰,是因为常看常新,是因为她有一整个相册的照片来记得她。
那孔黎鸢呢?
孔黎鸢在镜头里望。付汀梨也在镜头外望。
她盯着那双看起来似是一个矛盾漩涡的眼,恍惚地想
没有一张她的照片,没有任何影像,孔黎鸢又是怎么凭借那短暂的三天记忆,来记得她,甚至在这往复浮沉的四年后……
第一眼就认出,当时身上已经遭遇巨变,甚至还戴着口罩低着头的她?
第36章「昏暗电影」
她们赶到民宿,拎着那个摇摇摆摆的行李箱,携着簌簌往下落的雪絮,还有一身飘散四溢的羊肉汤味。
走进房间,就是一面窄仄的全身镜。
镜面陈旧糙黄,映着她们两身揉得皱巴脏乱的衣服、疲惫的脸色和风尘仆仆的姿态。
像一对拎着行李,在月黑风高期间逃难,然后又在公路中央扔下行李箱大吵一架分道扬镳,你恨我爱气势磅礴最后又把行李箱狼狈捡回来的苦命同路人。
不合时宜的比喻在脑子里浮现。
付汀梨对着镜子里两个模糊摇晃的人影笑出了声,她想起了被她用亡命鸳鸯形容的祝木子和祝曼达。
又觉得自己好笑,浑身上下都泛着钝痛,竟然还有心思比较。
孔黎鸢注意到了她的笑,从破陋镜面里盯着她看,
“你笑什么?”
“没什么,就是怕你住不习惯,地方太小了。”
付汀梨松了拎行李箱的手,把她们两个一起拎过来的行李箱摊在地上,随手把自己从市里拎的塑料袋搁在上面。
打量着这个小房间的环境。
民宿是向导在当地人家里临时租借的一个小房间,整个房间灰得闷。
顶上吊着一个昏的小灯泡,菱形格子瓷砖地面,整墙的灰黄色花纹贴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