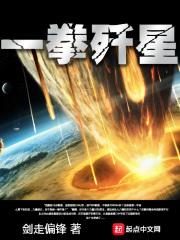言情小说>浪漫悖论全文免费阅读在线 > 漂亮朋友(第1页)
漂亮朋友(第1页)
那场下在1月1日的大雪完全消融,在上海也确实罕见,惹得剧组连着赶着拍了几天的雪景。
导演却还是不怎么满意,看微信大群里的后续安排,剧中有一个需要暴风雪的大剧情,光凭上海这点雪是做不到的。
人工造景试了几次又觉得不够真实,美术组和外联制片正焦头烂额,急着找这部分剧情的外景拍摄场地。
付汀梨的职责很明确,在现场就包揽有关雕塑部分的拍摄道具摆放、特写指导;每天收工之后就整理成文档给闻英秀汇报,每周抽空去一次闻英秀的工作室汇报,有些事情还是得当面说。
今天碰见工作室人手忙,便帮着闻英秀的一个学生打了半天纸浆。
学生是个好奇心重的,见她耐着性子免费帮忙。忙完擦擦手,过来问,
“听老师说你加州艺术学院雕塑专业的?这么好的学校?怎么回国还到剧组干个打杂的活?”
付汀梨很坦诚地答,“我家破产了,我妈负债,我被迫断供。暂时没找到其他工作,只能先干着。”
学生静了十几秒,干巴巴地笑笑,“哦哦是这样,我说呢,你一听我说就懂了,一下把我想要的纸浆打出来,打得比我描述的感觉还好……怎么,怎么跑去……干电影了哈哈哈——”
纯艺路难走,雕塑更靠名气和人脉。没有行业大佬带着,没有资金供着,前期很难起步。
最关键两个条件,付汀梨都不具备。一来她刚回国,根本不认识国内的行业大佬,就算之前那几个志同道合的合伙人,也跟她因为撤资的事情闹翻;二来,她也没资金,没有单干的条件。
刚刚是打杂,现在变成“干电影”。付汀梨笑了笑,问,“我这也算干电影?”
“怎么不算?”闻英秀的声音从身后飘来,瞥那学生一眼,“等电影拍出来,片尾名单都得加上你的名字。”
这倒是一种新奇的体验。付汀梨愣了几秒,“我?还加上我的名字?”
学生见闻英秀一来,喊了声闻老师,就笑嘻嘻地凑上去,
“闻老师,这位付学姐刚刚帮我好些忙,人怪好,你得给她多加几分。”
又凑过来给她眨眨眼,“我之前去你们学校交换过,所以喊声学姐没错吧?”
付汀梨没想到还有这层联系,弯了弯眼,“没错。”
学生笑了笑,又拍拍付汀梨的肩,跟闻英秀贫嘴几句就又去忙了。
付汀梨刚打了半天纸浆,没顾得上戴围裙,这会裤子和外套上都蹭了不少灰屑,有些灰头土脸,却不显得脏。
她就这样坦坦荡荡地站着,还笑盈盈地迎着闻英秀的目光。任谁看了那双眼,都觉得她畅快坦诚。
闻英秀瞥她一眼,“以后别干这些没用的杂活,给你发工资的又不是我,更不是我那个爱攒人干活的学生。”
付汀梨说,声音柔软清亮,“我知道,没关系的闻老师,就顺手一个忙而已,看见就帮了。”
她向来如此,心里没那么多弯弯绕绕,说什么就是什么。哪怕别人揣摩她的好心背后是不是别有所图,也不太想去在意。
如果连这种事都要放心上去,像烤串似的烤个来回,仔仔细细思量利弊,那不敢去帮忙不想去帮忙的事情也只会越来越多。
付汀梨发誓自己不能变成这样。
就算家里破产负债,她落魄到住廉价出租屋,再也触不及昂贵梦想。
也要守住这样坦然的心思,让发生在她身上的改变尽量延缓一些。
闻英秀“嗯”了一声,过一会,像是才想起之前那个问题似的,皱了下眉,提高音量,
“当然要加你的名字,好歹是个现场雕塑指导。”
顿了一会,又好似在强调,“虽然是加在我名字后面就是了。”
-
从工作室出来,又是那条美术街。
不知是不是因为新年刚过,人们都攒着汲取的节日温情,争分夺秒,迈入更紧凑的生存节奏。
这里便冷清下去,像是一场艺术电影放映结束,只剩下晦暗中微弱的光在摇晃。
付汀梨最近喜欢上这里,每次过来工作室都得驻足一会。
很简单的原因,这里和出租屋的对比很强烈,却又没有高楼大厦般会将人吞噬的不可控力。
是她能与艺术纠缠的最简单途径。
最关键,是免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