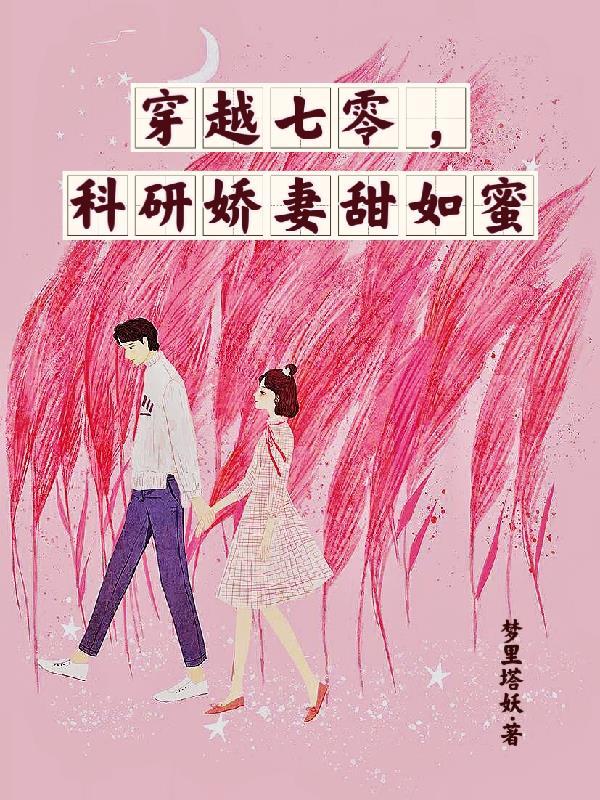言情小说>三国赵云是我弟弟 > 第6章 厚颜无耻(第2页)
第6章 厚颜无耻(第2页)
县丞善于察言观色,见赵厶神态稍有缓和,心头一喜,当即振奋精神,又变得神采飞扬起来,掰着手指头继续解释说:“譬如本县,不富不穷,算是个中庸之地,而县令秩四百石,倘或买,就值四百万钱。”
哦吼!
这么值钱。
赵厶吃了一惊。
“假如在此地任职三年,爱民如子又能如何?宵衣旰食又能如何?到头来还不是一贫如洗,空负清官之名。离开此地,又有几人认得?”显然县丞做不了清官,他这番话就有问题,明显对清官有意见啊。
“话不能这么说,做官之人,有为名者,有为利者,不能一概而论。”赵厶显然持反对意见。
那是当然,不是赵厶自夸,他就不爱钱,只图名。
县丞不置可否,却不露声色的恭维了一句:“似府君这等年少有为、文武双全之辈,久历沙场,军功显赫,自然不用花费分文亦能平步青云,我等小吏望尘莫及。”
“嗯!”这话听着舒心,赵厶又情不自禁自傲起来。
仔细想想,赵厶能当上中山太守,肯定是黄甫嵩的功劳。不枉当年跟他打黄巾,平西凉,如今受他保举,拿个一官半职,也在情理之中。满朝上下,赵厶也就服黄甫嵩一人而已。
“闲话少说,赶紧说正事。”好汉不提当年勇,赵厶回过味来,赶紧回到正题。过去的事不提也罢,还是眼前的事更要紧。
经过短暂接触,此时县丞也大概了解了赵厶的脾性,当下不敢造次,一本正经说道:“我等买官之人不同于府君,我们可是真金白银换来的官职,要说不心疼,那是自欺欺人。”
“哦?你这县丞之职也是买来的?”赵厶听出了苗头。
县丞一时语塞,自知说漏了嘴,登时羞得满脸通红。可事到如今,也没什么好丢人的,朝廷公开卖官都不嫌丢人,买官的丢什么人。
再说了大家都在买官,凭什么别人能买,他就不能买,对不对。这么一想,茅塞顿开,什么仁义廉耻全都不重要了。
“不瞒府君,我这县丞之职,俸三百石,合该三百万钱才能买下。因有人情,减了五十万,二百五十万就卖给我了。值!”县丞提起这件事相当自豪,看那神气的样子,赵厶都自叹不如。
“果然是个二百五。”赵厶不免在心里嘲笑他一番。顺带着又调侃一句:“你在此地任职多久了。”
话外意思是你花二百五十万买个县丞到底图个啥,上有县令压着,下有百姓之事顶着,两头不讨好。花这个钱冤不冤,是不是钱多没地方用了。
县丞却神秘兮兮地说:“时至今日,我在此任职刚满三个月。”
才三个月,有啥好高兴的。赵厶不理解,更加迷糊了。
“实不相瞒,这前两个月我也觉得这钱花的冤,可是这后一个月,我才明白,这钱花的值,太值了。”县丞想起此事,愈加自豪,愈加意犹未尽。
可是赵厶不理解啊,还得继续追问。
县丞说到兴起处,不打自招,全盘托出,甚至还有些得意洋洋:“之前尚有县令管着我,还有县尉跟我抢饭吃。现如今,他俩全都跟着叛军跑了,这无极县,可就是我说了算。”
嘶!
真是厚颜无耻!
赵厶突然好像明白点什么了。
“府君,别怪下官口直,说句不当听的话,您上战场杀敌那是无人能挡,可要说起这做官的学问,您还稍有欠缺。”县丞这是飘了啊,都敢称起下官来了。
“怎么个意思?”赵厶也来了兴趣。
这话实在太应景了,赵厶前世就一平头百姓,他哪知道做官的道理。只是常听人说官场如战场。战场形势复杂多变,赵厶自然懂,可是这官场,难不成比战场还复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