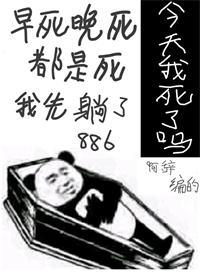言情小说>棉花爱人 > 第164章 法定回避事由2(第3页)
第164章 法定回避事由2(第3页)
成辛以果断摇头。
“这桩案子,我第一眼看到尸体的时候就觉得奇怪,弃尸的逻辑完全自相矛盾。”
他把之前和方清月蹲在尸体前的分析低声简要复述了一遍。杨天铭拿下嘴里的牙签,翻着白眼琢磨了一会儿,有些气愤地骂了一句粗话。
“草,凶手该不会是想把这桩命案彻底栽赃到方法医头上?什么仇什么怨啊这是?”
但成辛以似乎听得有些恍惚,怔了怔,看了看他,仿佛杨天铭的话又给了他某些新灵感,令他想起了什么,随即目光才又回到河对岸的棚屋方向。方清月和姚澄亮等人还没做完笔录,但他隐约看到鉴识科的一个同事刚刚走了过去,这令他的心再一次提了起来。
他喃喃重复,感觉自己的脑子“左右互搏”般地飞双重运转着,眼神逐渐恢复冷戾。
“……‘把这桩命案彻底栽赃……’老杨,你为什么要用‘彻底’这个词?难道还有不彻底的栽赃?”
“啊,我只是随便一猜。有啥问题吗?”
“暂时还没想到。”
杨天铭瞅他一眼,又兀自琢磨道。
“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凶手也太异想天开了。咱们警方做事再糊涂,也不可能光凭一条通话记录,就判定一个博士毕业的堂堂职业法医师是杀人犯吧?”
“所以啊……”
成辛以缓缓点头赞同,目露凶光,恶狠狠地咬住自己口腔内壁的肉,再次生生咬破,又再次将血囫囵吞了下去,咬牙切齿道。
“……我还能怎么办。”
杨天铭愣了愣,终于反应过来他的用意。
“你……该不会是在怀疑,凶手还有后招,不只通话记录,还想要再进一步搞出点什么来冤枉方法医,所以才这么干脆就撤下了所有咱们自己的人?”
成辛以没有否认,紧紧盯着河对岸。
“我是她丈夫,又是一队队长,有权指挥一队所有人的工作。所以一旦她涉嫌,不光我自己碰不得这桩案子,你们几个也碰不得了。如果凶手真的留了后招要继续栽赃她,我们的人越积极、干涉得越多,想给她脱罪、证明她清白的难度就会越高。”
“……我草……”
杨天铭听得出他嗓音里强力忍耐的焦虑沙哑,自己也不觉跟着有些忧心忡忡。
转念思忖片刻,杨天铭又低声问道。
“反正袁老爷子那边你可以放心,他很安全。我要不要,去盯一下徐墨?他正好赶在今天请假,也太巧合了。”
成辛以的眉心皱得死死的,视线依然凝在棚屋里做笔录的模糊身影,喃喃重复道。
“……徐墨……但方清月说得没错,当年‘7·26’案时徐墨确实没有作案时间,他不可能跟那桩案子有关系,也没道理会早几年就认识方清月……否则我一定早就查到了……怎么会呢……怎么会是徐墨呢……不行……”
毫无预兆地,成辛以轻轻叹了口气,视线未改,艰难吞咽喉咙,声音突然变得沙哑沮丧。
“……不行,老杨,我现在脑子有点乱,有点懵……让我再理一理。”
杨天铭转头看看他苍白锋利的脸庞轮廓,忍不住拍了拍他的肩。
“别担心,肯定没事的。”
话音出口,却又觉得这安慰的话毫无实际意义,又想了想,低声补充道。
“老成你知道吗,有软肋的人才有力量,为了保护想保护的人,才可以使出浑身的力气。你可以的。”
成辛以下颌微松,望着对岸,没再说话。
——
——
又过了二十分钟,姚澄亮和刘子宣从河对岸回来了,但方清月没跟在其中。
“怎么样了啊,方法医都问完了吧?”孟余急性子冲上去问。
姚澄亮看了看他,又和刘子宣对视一眼,没回答他,而是直接走到成辛以面前,面色严肃。
“老成,目前情况有点复杂,按照规定,我还不能让方法医走。我需要把她带回拘留室,并且暂扣她的通讯设备和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