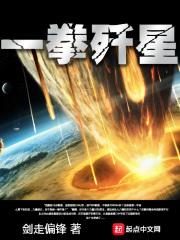言情小说>抱残成语 > 第37章 邀请(第2页)
第37章 邀请(第2页)
他还知道什么叫形势?还知道会生变化?
何楚卿只笑了一笑。
他和盛予其对俞悼河态度的不同就在这里,盛予其是个嘴贱的,不论俞悼河说什么都要半阴不阳地一顿贬,他自己也没讨好,时常为此挨揍。
何楚卿就不了,他只腹诽。
来虹海几年,他已经养成了不该说的就别张嘴的习惯。有些话,说给自己听,过个瘾就罢了。
何楚卿转身正准备离开,又听俞悼河在身后阴翳地说:“你不主动杀人,不会就觉得自己的手是干净的吧?何楚卿,你好好想想,哪庄哪件少得了你?”
何楚卿脚步一顿,没做回答。
他对俞悼河乖张脾性的纵容还有一个原因。
俞悼河小他三岁,这个年龄差巧到了何楚卿心里去——祈兴也比他小三岁。如果祈兴能活到现在,刚好也是成年。
载着两个人的汽车一路行驶到租界,最终停留在一幢三层洋房前。
这洋房的大小,即便是人丁兴旺的家庭,住着也不显拥挤。岳为峮无儿无女,只有一房小妾,两个人住也不知道嫌不嫌冷清。
何楚卿和俞悼河进门去,岳先生早已经恭候多时。
已经是深夜,桌上摆着几盘甜点。
二人热热闹闹地进门,倒是一点不见外,径直就落座在了岳先生两侧。
俞悼河忙活了一晚上,没来得及吃晚饭,拈过糕点就往嘴里塞。
两年来,岳先生仍是一般地慈眉善目,精神气尚好,不显老态。
他皱着眉看俞悼河,略遮了下鼻腔,道:“定甫,你又去哪里弄了一身腥臭味?”
俞悼河狼吞虎咽没来得及回话,何楚卿把眼镜一摘,挂在衣领,看热闹不嫌事大:“先生,要我说么?”
岳为峮一挥手:“说。”
“他处理了花钱雇绺子劫走盛予其的那个人。”何楚卿故意扭曲意思。
岳先生一听,为他这突如其来的友爱而感慨,不再提这话茬了,而是问:“是谁干的?”
俞悼河有口难言,噎了满嘴糕点,一脸吃了屎似的的表情。
“姓。。。吴?好像跟我们有过利益纷争,半年前了,我有点印象。估计是特意等到自己没有嫌疑了,才敢干这种事给您添堵。谁知道,被俞悼河逛窑子听见了。”何楚卿趁着俞悼河不能张嘴,抓紧时间抹黑。
岳先生果真没在意前因,只又警告俞悼河说:“你刚几岁?那种地方以后少去。”
俞悼河狠狠瞪了何楚卿一眼,何楚卿笑的前仰后合。
“今天已经很晚了,把你们找过来,主要是有一件急事——顾还亭司令,带着几万的虹海驻防军进城了。这事,你们知道吗?”岳先生正色道。
何楚卿登时收敛了笑意,若无其事地点了点头。
奇了,还真让俞悼河说中了。
“现如今,毋宁被绑架上了山,且不说这伙绺子是从何而来,往后这条商路恐怕没人敢走。”
何楚卿心里一动,立马懂了:“您是说,给司令一个顺水人情么?”
岳为峮点了点头,又给俞悼河解释了一遍:“我们以自己的名义,请求顾司令出兵平山匪,维护虹海的贸易。这样一来,顾先生在虹海商会、乃至整个虹海的百姓心中,都算颇具份量。而我们,既省了财力,还搭上了顾司令这层关系。”
俞悼河满不在乎地问:“您不怕盛予其真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