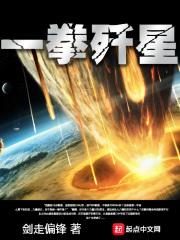言情小说>炮灰真少爷科举升官日常免费阅读 > 第59頁(第1页)
第59頁(第1页)
「幹活?」
魏思武咀嚼了一下這個詞,別有深意道:
「慶陽幹得,我就幹得。」
徐瑾瑜:「……」
想想趙慶陽用著趙家劍法,咻咻咻的劈竹絲,而一旁魏思武用分絲器跟踩縫紉機似的劈竹絲,徐瑾瑜一時有些神情恍惚。
魏思武這邊被徐瑾瑜不經意間順好了毛,不彆扭了,趙慶陽也是個爽朗性子,一干少年人很快就嬉鬧在了一起。
很快,不知道是誰提起:
「這兩日我爹管的越來越嚴了,今個出來還是我磨了我爹好久呢!」
「嗐,誰說不是呢?還不是武安侯家的事兒鬧的!」
徐瑾瑜聞言正中下懷,只裝作好奇道:
「諸位口中的武安侯家之事究竟是何事,竟能讓諸多勛貴都緊張不已?」
這事兒也沒有什麼不能說的,只茶樓里關於這件事兒都有幾個版本,但二代們手裡都是最消息:
「那武安侯行伍出身,整日泡在軍營之中,兀那鄭石打小被家裡的婦人嬌慣,一有不順心就喊打喊殺,在京里別提多招人嫌。
以前啊,武安侯府的老夫人逢人就說,鄭石這是有乃父之風……」
說話的少年口中的「乃父之風」怪腔怪調,惹的眾人哄堂大笑。
「莫急莫急,還沒完,那鄭石頑劣不堪,小小年紀就知道摸人家姑娘的臉,現大理寺少卿的長女十歲時就曾被他摸了一回,現在都送回老家三五年了。
官員之女,尚無法避開他的欺辱,何況民女?而這次狀告他的,正是三年前被他欺凌過的民女。」
那人說到這裡,聲音陡然變得沉重起來:
「據那民女口述,三年前,鄭石與她偶然一見,便心懷不軌,尾隨至家中。
卻不幸被那民女的兄長撞到,鄭石索性直接讓護衛壓著那民女一家祖孫十八口在院中,讓他們親眼看著自己如何欺辱了那民女……」
徐瑾瑜聽了這話,端著茶碗的手停頓片刻,心下一沉。
可還不待他細思,那人便繼續道:
「之後,鄭石許是覺得留著那民女一家會是隱患,所以……痛下殺手。」
「其實,這裡頭我最好奇的是,要是這麼說,那民女又是怎麼果下來的?鄭石既然想要斬草除根,自然不會留有後患。」
「鄭石當然不會給自己留有後患,他與那民女雖有露水姻緣,可卻下手很辣,當胸一劍,本該一劍斃命!」
二代們聽到這裡,也不由面面相覷,他們雖然不干正事兒,可也不敢玩兒這麼大!
那可是一十八條人命!
「那,那民女如何活下來?」
「哈,巧合的是,那民女的心房位置與常人相悖,僥倖存活,此乃天亡鄭石!
三年時間,那民女休養生息,只待今朝,擂鼓登聞,以達聖聽,求個公道罷了。」